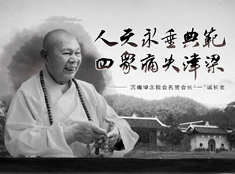内容提要:本文以《说革命》《心理革命》《革命当从革心起》三篇文章为文本基础,对太虚法师的社会革命观进行了梳理、总结和分析。本文认为,太虚法师的社会革命观以佛教为本位,不仅以佛教的信仰为前提,以佛法的实践为归宿,而且还体现在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以及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态度上。太虚法师积极关注革命,既体现了他的护教热情,也体现了他实践菩萨行的救世情怀。他既进入革命之中,又独立于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潮之外冷眼旁观,从而看到革命的多重面孔。
关键词:太虚;佛教;社会革命;心
作者:秦萌,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出家人无论是了生脱死还是弘法利生都要立足于世间,以此为起点来上求佛果,下化众生。所以当割爱辞亲、剃发染衣以求与世间保持距离的出家法师遭遇革命洪流的时候,心灵的泰然自若并不能代替行动上的种种努力以应对世事无常,保证佛教在世间的生存和发展,对革命积极或消极的“参与”也就在所难免。今天,我们来重新倾听这些被抛入革命大潮中,甚至要被革命潮流“必然”淹没的人物当时遭遇革命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对我们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佛教对这一进程的参与、回应与影响,必然具有积极意义。
太虚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两岸四地佛教界所走的道路都受到太虚法师的影响。而太虚法师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史难以绕开的人物。太虚法师对传统佛教发展到近现代所滋生、累积的种种弊端和由此造成的衰败状况痛心疾首,早年曾极力鼓吹“佛教革命”,希望以激进的改革复兴佛教,冲刷掉附着在佛教肌体上的沉渣积垢,因而有“革命僧”之称。在这里笔者想谈的并非太虚的“佛教革命”理论,而是他作为一个佛教出家僧人对社会革命的思考和看法。因此,本文选取了太虚法师的《说革命》《心理革命》《革命当从革心起》三篇文章作为讨论的文本依据。
一、佛法是最彻底的“革命”
在《说革命》一文中,太虚法师认为,革命党发一通宣言宣布革命只能算作“命令的革命”,只是发革命之心而已,还不能算革命行动。真正的革命,在于“生命的革命”,也就是革去旧势力旧习惯的生命,使新政权、新势力的生命得以诞生和延续,因而革命是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需要革命者以高度的智慧和慈悲的胸怀为指导不断奋斗才能取得成功。否则,革命只能是“扰乱一时”的闹剧而已。太虚法师还指出“凡事物之革去故而鼎取新者,皆可赋予革命之名”,因此,革命不仅包括如政治革命之类的“人事革命”,而且包括变革人及一切生命自然本性的“自然革命”,进一步说人之本性的完善必然带来社会政治的根本变革和完善,因此“自然界革命能包括人事革命”。佛法能使一切有情从不觉走向觉悟,从而根本改变人及一切生命的自然本性,“能彻底于自然革命”。因此,文末太虚法师以口号式强烈而坚定的语气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皆趋向佛法之彻底革命为究竟。不知佛法彻底革命之真义而违反之者,终将为最后之反革命;故真正主张彻底革命之人士,必须于佛法有完全之信解”!
太虚法师对佛法革命性的强调,恰恰表明当时的佛教已经被当作革命的对象而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说革命》一文作于民国十六年六月(1927年6月)的上海,发表于《海潮音》第六期。当时正值大革命高潮,《太虚大师年谱》记述:“时教难因革命军事扩展而日益严重。……(1927年,民国十六年)三月,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南京。南京法相大学解体;内学院亦陷入窘境。时张宗载西抵武汉,忽以锄奸名义,遍发传单,大骂僧尼,诬加罪状。……”如果再不振臂高呼,澄清佛教的革命本性和革命立场,佛教难免要成为国民革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了。因此,《说革命》一文中鲜明的护教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用佛法来诠释革命或者用革命来诠释佛法,尽管是迫于环境的方便法门,但这种诠释并非毫无道理的牵强附会,而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这表明佛法本身强大的理论融摄力和生命力,说明即使在革命浪潮中,佛教也并非只能坐以待毙,佛教这一陈酒是可以装进革命这个新瓶里去的。同时,也正因为将佛教诠释为革命只是一种方便法门,并没有动摇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信仰,因此,太虚法师对革命的“参与”和“迎合”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站在佛法的立场上来静观和反思革命的意味。面对辛亥革命以后接踵而至的复辟与革命的反复斗争,太虚法师以佛门比丘的救世情怀和佛教的独特智慧,诚恳而又冷峻的传达出这样的意思:盲目的狂热和出于私心的投机只能带来闹剧和灾难,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和国家的和平安定。
二、心理革命为改革之策源
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太虚法师在西安新城大楼应邀作了题为“心理革命”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太虚法师明确提出了“心理革命”的理念。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为了个体的生存发展而互相争夺。站在佛教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来看,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实际上就是损人以利己,这可以是人们生活的现实状态,但决不应是理想状态;这种现实状态只是“相续生活之习惯”,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因此从广义上来说,革命就是改变损人利己的“相续生活之习惯”,从而使一切众生都得到安乐。为生存而互相争斗必然造成人生的痛苦,引发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改革的渴望,而世界又是变化无常的,因此一切都可以改革。这就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接着,太虚从西方科学学科划分的角度出发,认为革命可以分为物理革命、生理革命和心理革命。按照佛教的“唯心”观点,“人生世界皆以心为主动力”,因此,“须由最基本之心理革命以为改革之策源”。
相对于大革命时期“教难”的紧张气氛,此时佛教的生存环境已有所改善,但是太虚法师在《心理革命》的演讲中,继续了《说革命》一文的佛教本位思想和护教弘法立场。太虚法师面对听讲的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纵论古今,侃侃而谈,在整篇演讲中他很少直接阐述佛教的道理,却时时刻刻体现佛法的根本精神。他在来自西方的思想和话语系统中游刃有余,不动声色的将西方的所谓“近世文化”批判吸收,纳入佛法的体系之中,作为佛法的注脚和载体。
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早对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有一种超越而通透的理解,所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佛教的真理或者说万有的实相超越语言之上,语言最多只是指向真理之月的手指,而不是真理本身。即使在革命语境中,佛教也不必过于恐慌,如果坚信佛教的真理性,那么革命的话语同样可以用来巧妙的变成佛法的传达者和表述者。这一方面靠佛法本身的融摄力,一方面则取决于诠释者的智慧。正是这种自信和对语言的超然态度,使传统的中国佛教在面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浪潮、革命话语的讨伐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之时,可以比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为镇定从容,更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三、革命当从革心起
《革命当从革心起》是太虚法师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在常州中山纪念堂发表的一篇演讲,是他的社会革命观最完整、最严谨的理论表达。在这篇演讲中,太虚继承了“心理革命”的思想,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述了“革命当从革心起,由革心而成革命”的主张。演讲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说起,以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对心理建设的强调来印证“革心”的重要。他透彻的分析了“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由来和含义,提出革命的今义包括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三种意思。其中的社会革命其实就是太虚法师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太虚法师从佛教“唯心”理论出发,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皆从人心的思想转变出来”,个人的生死、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都是以人心为依据,都由人心转变而来,所以“革心是因,革命是果”,由革心而革命,从而实现内圣外王。
以佛教的理论为依据,太虚阐述了他对“心”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心有两层含义:一是潜通的精神界,也就是佛教所说的“阿赖耶识”;二是显著的心理作用。“潜通的精神界”潜在于显著的心理作用等“一切动作”之下,是显著的心理作用和人类种种行为的内在原因。这种内在原因,既潜在于个人显著的心理作用之下,又能彼此感通、交互影响,因而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必然影响到他人和社会。最后,太虚法师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了革心的方法——大乘佛教的“六度”。对心的分析正是革命当从革心起的理论依据。这篇演讲充分显示了太虚视野的开阔、学养的深厚、治学的严谨和思想的精深。
四、结 语
综观上述三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太虚法师费尽心思反复说明的其实只有一个道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以“心”为根本,都是从“心”转变出来的。“革命”是世间的万事万物之一,因此,革命也应当以革心为根本,革命当从革心起才是最行之有效、最为根本的,而最彻底的革心之法莫过于佛法,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是一切革命的起点和归宿。
太虚法师的社会革命观是以佛教为本位的。这不仅表现为以佛教的信仰为前提,以佛法的实践为归宿,而且还体现在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以及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态度上。他颇为独到的将革命划分为“命令的”和“生命的”,认为发布革命的命令只是表示要进行革命,只是发革命之心,只有真正的革命行动才是行革命之行。从发心和实行两发面来考虑问题恰恰是典型的佛教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革命有助于冷却革命的狂热和对革命的盲目崇拜,革命从根本上说是旧习惯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并非一次横扫一切的激烈运动就能改变一切,革命的暴风骤雨之后更需要艰苦的建设才能真正改变“旧习惯”,使革命的成果深入人心获得生命。对“人心”问题的突出强调,也是佛教独特而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尽管这难免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颠倒论调,但是它指出了流行的革命理论偏重于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革命,将一切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的不足之处,起码可以为我们今天反思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另外值得参考的思路:理想社会的构建、人生幸福的获得不是单靠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就可以一蹴而就、彻底实现的;没有心灵的净化、道德的提升,要实现幸福人生和理想社会恐怕也举步维艰。
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太虚法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满怀自信的指点江山,运用自如,他以佛法的超然智慧驾驭现代西方的话语体系,试图通过佛法与革命的互释来融摄和引领现代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将其纳入佛法的体系之内,颇得中国古代佛门大德判教思想之妙,也为中国传统佛教的现代诠释和转型,乃至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中西文化的对话融合,提供了一条值得参考的道路。
身为佛门比丘的太虚法师积极关注革命,关注社会现实,这既体现了他的护教热情,也体现了他实践菩萨行的救世情怀。他深知只有展现佛教的救世价值才能真正护教。总之,作为一个遭遇革命的佛教僧人,太虚法师要全力护教,要慈悲救世,因而他必然进入革命之中,但坚定的佛教信仰又让他能时时独立于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潮之外冷眼旁观,从而看到革命的多重面孔。这也是我们应该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