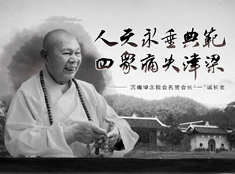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推动者,太虚大师一生提出了许多佛教改革理念和构想,其中,建立全国性佛教统一组织是他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他提出的教制革命和整理僧伽制度的成功与否。在太虚大师一生中,特别是普陀闭关以后,他倡导成立或参与的佛教组织有中华佛教联合会、中国佛学会、中国佛教会等。对太虚大师与这些佛教组织的关系及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维度帮助我们理解太虚大师所从事的佛教革新运动。
关键词:教团组织 中华佛教联合会 中国佛学会 中国佛教会
作者简介:明杰,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禅》杂志主编
在太虚大师的僧伽制度改革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团组织的建立。太虚大师僧制思想的根本要义是要结合住持僧伽与社会信众,经由僧伽领导,建立适应新时代的僧伽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太虚大师具有建立全国教会的雄心,这无论从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参考日本佛教宗寺制度,还是仿效天主教的辖区设置县、道、省不同级别的弘法机构,乃至建立最高级别的“佛法僧园”的构想中,都可以体现。“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制度化的宗教组织,团结全国各佛教寺院,增强佛教话语权和教团协作力。”
一、团结与更新:建立全国性教团组织的设想
终其一生,太虚大师始终重视佛教组织的建立。从早期的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等未能实行的主张,到中后期不断争取、不断妥协地参与教团组织的联合,这或许是因为在太虚大师眼中的佛教是全中国整体的佛教,断不肯从局部而影响全体,必须要从整体架构上来宏观施行。
太虚大师在普陀闭关结束后,对日本佛教进行了考察,得出《整理僧伽制度论》的设想具有日本佛教分宗的长处,没有其各自为政、信仰力量分散的短处,但事实上,“中国佛教向来亦缺乏一个联合各省的统一组织机构,甚至连各地方僧众的联合团体也没有,各地寺院都是分散,各别独立,形成各宗寺单打独闯的局面;所以太虚大师在民国初期,即有倡议‘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或参与‘中华佛教总会’等机构的组织。”
“团结”意识是太虚大师实现整理僧制的关键性前提,无论组建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的失败,还是参与中华佛教总会等机构的种种波折,太虚大师都从未放弃建立统一佛教组织的努力,不得不说是因为他心目中始终存着“佛法僧园”的理想。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太虚大师将“佛法僧园”作为联络全国八大宗寺的最高机构,其实就是他团结意识的产物。江灿腾认为“佛法僧园”的伟大构想“实在是佛教史上的理想国,以中国现代思想出现的新姿态”,同时也认为“佛法僧园”设立工厂、银行是令人佩服的务实一面 。
早在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成立佛教协进会并引发“金山事件”,使得协进会终告失败,但在太虚大师看来,努力并非白费,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佛教总会之所以成为佛教的统一机关而且分会林立、发展迅速,“未始非协进会为之反动力原动力之所致也” 。民国初年,因寄禅以身殉教,中华佛教总会而得以核准成立。虽然太虚大师自己也曾努力建立佛教组织,但在他思想里,“统一”的意识非常强烈,这一点在《上佛教总会全国支会部联合会意见书》有明确的表达 。在太虚大师的心目中,这样的统一组织可以维护佛教僧寺的财产,因为全国佛教的寺僧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才能掌握寺院财产的所有权,从而避免寺院财产被侵夺的隐患 。到了1915年,佛教总会因《寺庙管理条例》的颁布而被取消 ,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晚年的太虚大师仍未放弃建立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努力。1946年8月,在焦山出席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会务训练班结业典礼上,太虚大师仍在强调建立全国性佛教组织的重要意义 ,太虚大师还向在场的年轻僧伽(星云法师当时即在会)提出应以全国佛教会为出家僧伽的“第一生命” 。除了初期改革运动中成立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等努力,太虚大师在后来的佛教改进运动中,还尝试成立中华佛教联合会,建立中国佛学会,参与中国佛教会以实现整理僧制、振兴佛教的理想。
二、理想与现实:中华佛教联合会的呼吁
中华佛教联合会可能是太虚大师在庐山大林寺暑期讲习班无心插柳的结果。1922年秋天,严少孚在江西风景名胜之地庐山以恢复大林寺名胜为由,修建讲堂,粗具规模。次年(1923)7月,太虚大师偕王森甫、史一如至庐山,主持暑期讲习会。23日(“六月初十”),暑期讲习会正式开讲,太虚大师讲“佛法略释”“佛法与科学”“佛法与哲学”“佛法悟入渐次”,黄季刚、汤用彤、张纯一皆有演讲,历时二十天(8月11日结束),令在庐山的外国基督徒和日本来华人士惊异。
起初,严少孚自作主张的在大林寺讲堂前,竖立了一块“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木牌,这一举动很快受到了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圆成和在庐山的日籍人士的注意 。日本领事江户以日本佛教徒名义来参加,并致电日本国内,约定明年派代表参会。太虚大师于是在大林寺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并著手筹备第二年(1924年)召开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即由此开始。
1924年7月,“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大林寺召开 。会期三日(7月13至15日),商讨了中日交换教授学生、联合缅甸、泰国等国佛教的议题,并最终议决第二年在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实际上,三天的会期中,第一、二日开二次预备会议,仅中国代表参与讨论。太虚大师在预备会议上提议应分三个步骤进行:一、中国国内各省的联合;二、东亚有佛教国家的联合;三、将东亚佛教精神传播到欧美各国,成为事实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太虚大师坦言“此时不过理想而已”。同时,太虚大师提议,到会五省代表 (“陕西康寄遥居士有信来,并之则有六省”)虽只是少数,但可以到会各省代表商议组成中华佛教联合会,以后请其余各省加入 。然而,这样一种代表的构成是否足以组成中华佛教联合会?先不论太虚大师提到的了尘、性修、常惺等僧伽代表,江西李政纲、四川王肃方等在家信众是否可以代表其所在省份的佛教界?这充分反映了太虚大师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其实,太虚大师自己是清楚的,“初组织此世界佛教联合会原属理想而已,中国国内尚无联合,何况世界?” 或许在太虚大师心中,如能有机缘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可以促进中国佛教的内部联合?
根据太虚大师在《自传》中对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的记录,其中有“这个弄假成真的世界佛教联合会,总算开得已有了一个雏形” 的话,这里的“弄假成真”也许正反映了太虚大师的真实想法。
因为并不具备真正召开世界佛教会议的条件,因此,第三日(7月14日)的会议是中日代表联席会,主要讨论第二年(1925年)在日本召开会议的事项,太虚大师提出名称为“世界佛教联合会东亚会议”,而日本方面,则出于日本佛教界实际的复杂情况,以“有名实不符之嫌”为理由,主张名为“东亚佛教联合会”,最终太虚大师以“商议名称表显中国人之理想与日本人之实践,各有精神。然明年开东亚佛教联合会所抱理想依然是世界的”,结束了双方的争议 。
在随后召开的中华各省代表联席会上,明确首先应成立中华佛教联合会。而实际上,太虚大师等人仍以“世界佛教联合会”名义向政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湖北督军公署申请立案 ,很快(8月)即得到督军公署的同意。后来,因广东等寺庵财产遭到变卖,太虚大师即以刚获准成立两个月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名义向内务部呈文,请求“均作无效” 。
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后,太虚大师积极行动,与李隐尘等发起筹组中华佛教联合会,以合法推举代表出席东亚佛教大会。1925年4月,太虚大师与白普仁喇嘛、庄蕴宽等人,在北京设立了“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 ,据该会呈请内政部备案文,“先设一筹备处,派代表赴各省县,由县联合会进而为省联合会,由省联合会进而为全国联合会” 。经过努力,“各省之佛教僧俗徒众,分途进行,县会省会,渐告成立” 。见诸《海潮音》的各地佛教联合组织,有京兆佛教联合会 、中华佛教湖南联合会、顺德中华佛教联合会、岭东佛教联合会、中华佛教联合会岭南支会、潮梅佛教联合会筹备处等。当时,内务部拟定的僧道庙产整理办法,可能也加速了全国佛教联合会的成立 。
在组织佛教联合会的方式上,太虚大师有自己的想法。总体来说,是主在家、出家分组而后合组,“重在出家佛教僧与在家佛教徒之由分组而合组” 。这贯穿着他之前住持僧整理僧伽制度、在家信众组织佛教正信会的主张,实际即是佛教住持僧与佛教正信会的联合。太虚大师认为,出家与在家二众的分合各有利弊,“混合而不分途组织,既多互侵互乱之弊;分组而不联合,又成相隔相碍之患” ,中华佛教联合会注重分组而合组则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太虚大师的主张中也存在与传统佛教相矛盾之处,如他强调佛教正信会的作用,认为“佛教住持僧在提高佛教中实行实证之少数人人格,以住持佛教……但有住持僧之出家行法,则不足以普及一般人民,而不能摄受大多数国民皆为佛教信徒” ,而正信会“则在普及佛教于一般人民起其信仰而摄化之”,“佛教在民众失其基础,必难存立安固,故须有正信会以广摄之” ,将住持僧与正信会结合来看似乎没有问题,但分别而论,他对于住持僧的理解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影响颇大,另一方面就是过分突出了正信会的作用。再者,正信会往往以个别僧人为导师,佛教岂不成为少数人领导的佛教,与佛教重僧团的本义似有不符。
与当年成立佛教协进会等组织时的境遇天壤之别,中华佛教联合会的成立得到了上下的响应,虽非一致,开端也属顺利。中华佛教联合会成立后,显荫法师在致太虚大师的信中称赞该会“对内对外皆为必要之良图”,同时提醒太虚大师注意日本对华布教的意图 。1925年10月,以太虚大师、道阶法师为首的二十六人组成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出席东亚佛教大会。
虽是因应时势的需要下成立,太虚大师逐渐以中华佛教联合会实现自己联合全体佛教界的意图。除了组织代表出席东亚佛教大会的短期任务以外,中华佛教联合会也发挥了一定的团结、纽带作用。一时,佛教界颇有生气。但是,团结仍是中华佛教联合会能否长期存在的首要问题。显荫法师即曾提出十条建议,如联络全国各丛林长老协同进行,聘请诸山大德为理事等,并特别指出“观贵章程,诸山长老甚少,当急宜多联络” ,可谓切中要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该会为出席东亚佛教大会而仓促联合组织,未能密切联系当时保守派的诸山长老,致使联合会如昙花一现,在日本之行后,即销声匿迹 。
中华佛教联合会的存在虽然短暂,但这种由政府明令核准成立的佛教组织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潮安县知事致中华佛教联合会书》 就是关于潮梅地区寺庵财产问题给中华佛教联合会的公函。
三、预想与变通:中国佛学会的成立
1928年3月,内政部长薛笃弼支持改佛教寺院为学校的主张,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也作了《庙产兴学问题》,拟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议案,佛教界大受震动。《现代僧伽》社等呼吁反对。太虚大师因此前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而有的影响力,发表文章对邰爽秋等人的主张加以驳斥 。当时的佛教界气氛空前紧张,连专心净土的佛教大德印光法师也开始考虑僧制的问题。
中国佛学会的成立与此一情势有直接的关系 。同年的6月23日 ,因太虚大师即将远行欧美,蒋介石邀请其赴南京见面,太虚大师得以借晤谈的机会,提出组织佛教团体的想法 ,蒋氏赞同太虚大师的想法,作函 介绍太虚大师与国民政府的要员谭延闿等人洽商进行 。太虚大师的本意,是要发起全国代表会议 ,成立“中国佛教会”,而蔡元培、张静江等人认为此时不便提倡宗教,以设立佛学会为宜 。据林子青的说法,蔡元培的建议便于吸收不信仰佛教但又从事佛学研究的人士参加 。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会会名说明》中,解释了接受这一提议的想法:“佛教之教字,本指‘言教’,与今语‘学说’同义;以学代教,理无不可,而能较顺时代之心理。至先设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然中国佛学会会章,仍待全国佛教代表会议议订,亦不违原议也。”
由于有蒋介石的介绍和支持 ,太虚大师很快的(7月28日)于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开预备及筹备会三日,决议数项内容 ,其中的“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以最短时间“养成整理寺院,服务社会”的人材,分配到各处佛教团体工作 。
太虚大师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要员争取,向内政部等机构呈文,另一方面也号召全体僧伽,发表《恭告全国僧界文》,以决先组佛学会,催开佛教徒代表会议。至此,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佛教始有正式组织的雏型,然而,遗憾的是,“尚不能揭出‘佛教’名义,其艰苦何如!”
在此前的《条陈整理宗教文》中,太虚大师即对他理想中成立佛教组织的办法进行了阐述 。这次成立佛教教团组织,太虚大师吸取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冀望于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以建立县、省、中央三级的佛教统一组织。同时,关于僧俗分部方面,仍然延续了《整理僧伽制度论》最初的思想和建立中华佛教联合会时的主张,强调住持僧与在家僧众应加以区分。居士林等已有的在家信众组织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全部加入统一的中国佛学会,并接受其指导和整理。“统一”始终是太虚大师建立佛教组织的根本思路和目标。
在夏季召开第五次中央执监会议时,太虚大师又针对各地方出现的种种障碍 ,提出三项请愿:全国佛教团体之组织、保护全国寺产、认可佛教僧众之职业,这三点内容反映了太虚大师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
在屡次的呈文或条陈中,太虚大师申明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依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纲领,中国的佛教也应以三民主义为准绳,革除帝制时代的各种劣习,建设适应时代、符合三民主义的新佛教,以发扬大乘佛教的真精神。始终强调佛教僧徒在三民主义的社会中应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反映了太虚大师在当时寻求佛教住持僧伽社会生存空间的意识,而前提则是“非有全国佛教徒严密统一之组织,不足以完全实现”。在《发起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的提议》中,首要的“目的”即为“议决各种整理僧寺之方案”、“议决各信众团体组织之方案”、“议决僧众与信众之区别与关系”,这仍是太虚大师毕生为之努力的精神——“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虽然太虚大师在团体名称上接受了政府(要员)的意见,定名为“中国佛学会”,但这一组织仍是按照“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的目标来建立的,“首都设中央部,省设省部,县设县部,以为决议执行一切佛教事业之法团”更非一般所谓“佛学”团体所能担负的职能。
虽然名为“佛学会”,也确实从事许多讲学工作,但太虚大师理想中的组织仍是能够对佛教的振兴负有领导的能力,如他在《佛教僧寺财产权之确定》中就假设一个“中国佛学会”作为全国佛教徒统一组织以行使管理僧寺财产的权利 。太虚大师的改革始终离不开佛教寺产的整理,这关系到佛教的经济命脉,很多问题都是由此生发。所以,太虚大师的“中国佛学会”一定要在僧寺财产方面拥有话语权,进而获得管理权。
在筹备处成立后,太虚大师1928年8月11日启程赴欧洲,开始了筹备三年之久的欧美游化,历时八个月。中国佛学会也因太虚大师出国不能亲自主持而出现精神涣散的状况,致使计划中的各项工作无法“赓续举办” 。直到太虚大师回国后的1929年11月29日,中国佛学会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太虚大师当选为会长。此时的太虚大师也开始意识到新旧两派的分歧和矛盾 ,决定专心致力于世界佛学苑和中国佛学会的建设 。
中国佛学会既名“佛学”,确实也开展了很多佛学演说,如举办“星期研究会”、举行佛学座谈 。太虚大师本人在中国佛学会也曾讲说《心经》、《圆觉经》、《三十唯识论》等。为了更好的进行宣传工作,中国佛学会还出版《新报•佛学周刊》,该刊1934年创刊,由蒋微笑、释大超担任编辑,是《新报》的周刊,随《新报》发行。
在组织架构上,中国佛学会采取分会制,在上海、厦门、成都、九华山、汉口等地成立了分会。某种意义上,中国佛学会设立分会也是在吸纳之前中华佛教联合会散处各地的力量,如推定式如、根宽、欣西、李兰甫等四人为广东省佛学会筹备员,根宽即为汕头岭东佛教联合会会长 。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学会还曾发展有海外分会,不得不说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世界佛教运动的一项成果。1933年佛诞日,由华侨陈德清、叶宏经等发起,仰光中国佛学会成立,请太虚大师学生慈航法师主持指导,发行有《慈航月刊》 。该会曾向圆瑛法师约稿,圆瑛法师在复函中赞叹“开我国佛教二千年来之流通纪录” 。另外,新加坡还有星洲中国佛学会。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学会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中国佛学会还曾呈文国民政府内政部,请陆军总司令部电令各地受降部队要切实保护佛教僧众和寺产,不许任何人强占,并得到“已转令各受降部队切实保护” 的答复,这体现了中国佛学会维护佛教权益的积极努力。中国佛学会最后一次见诸《太虚大师年谱》是1947年5月25日,该会与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暨南京市佛教会联合为会长太虚大师举行全国性追悼会 。
四、中心与边缘:中国佛教会的博弈
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会的纠葛比较复杂,涉及新旧派矛盾、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无意于做过多的梳理和探讨,只是以中国佛教会作为太虚大师建立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又一尝试,略为涉及。
太虚大师游化欧美期间,中国佛教界有感于《寺庙管理条例》的严苛 ,由在南京的中国佛学会联合圆瑛法师所领导的江浙佛教联合会,共同发起、召集了十七省的佛教代表,共聚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并拟定了《中国佛教会章程》,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内政部备案,请求政府修正《寺庙管理条例》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29年4月12日,同月的29日晨,太虚大师才经日本回到上海。6月3日,太虚大师在上海出席了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监委员会,被推举为常务委员。按照太虚大师自己的说法,他自欧美游历回国时,已当选为中国佛教会执委、常委之一,虽然觉察到这个中国佛教会也是一“保持寺产之集团”,但仍抱有维护佛教并渐进改革的期望,因此才“委顺曲协,挈携偕进” 。实际上,由太虚大师发起的中国佛学会还是在当年的11月举行了成立大会,只是因为已有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在先,中国佛学会的存在不能如太虚大师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可以说,太虚大师因为游历欧美而错失了成立中国佛学会的良机。虽然中国佛教会非太虚大师主导成立,但既然被选为常委,太虚大师仍然抱有乐观的期望,决定“委顺曲协,挈携偕进”。太虚大师一直努力于建立中国佛教教团组织,按照印顺法师的说法,《中国佛教会章程》先期由太虚大师与王一亭联名致书,并且由王一亭亲谒蒋介石,才获得内政部准予备案 。王一亭在致太虚大师的信中也强调“凡事全赖实行,决不以空言了事……将佛教会及佛学会有一种真实办理,与佛教真宗旨行持,大家出来用精神上财力上合作统一整理之” 。
只是这种“委顺曲协”的时间其实并不长,1929年12月,太虚大师即在《海潮音》刊发启事,宣称“今于不能常川驻京沪之故已再向中国佛教会函辞常务委员及学务委员长之职,特此布闻,统希垂察” 。不过,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会的关系并不那么容易切断,这或许还是因为他心中那个中国佛教统一团体的理想。1931年,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会旧派代表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
近代历史上中国佛教界的几次组织和联合都与外部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1930年11月1日,中央大学邰爽秋等人成立庙产兴学运动促进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危及佛教界的庙产兴学运动又再次兴起。“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呈请拨庙产兴学案”甚至通过了国民党全体会议的议决 ,于是,渐归平静的佛教界又一次震动,中国佛教会、《现代僧伽》社等机构一致呼吁反对。这也促使佛教界进行思考,“大都已认为佛教非根本整顿不可,故大多都一致主张督促中国佛教会召开全国佛教徒大会,解决彻底整顿内部的办法,这样的众心一致,是很难得的。” 在社会形势的变化,亦或太虚大师多年奔走、呼吁整理僧伽制度的影响下,虽然在整顿佛教的方法上不一定全然接受太虚大师所提各项,而佛教界已逐渐形成整顿佛教的共识。
经过了出关后十余年的时间,虽然当年金山事件的影响不一定全部消除,但太虚大师的佛教领袖形象和地位逐渐形成和确立,这一方面因为太虚大师的能力和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与太虚大师能够获得国民政府要员的支持也有极大的关系,他被人们视为解决危机的当然人选 。
在后来召开的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上,太虚大师一系获胜 。会议改选的结果,太虚大师等十七人当选为执委,而保守派的黄健六、钟康侯等落选,“一向包办操纵之沪杭名流失败”,“新旧之间,显然趋于破裂” 。在中国佛教会第三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后,太虚大师与仁山法师、王一亭、谢铸陈等人全部接管中国佛教会,并将会本部移至南京毗卢寺。
太虚大师一系主持中国佛教会后,最大的成绩应该是争取国民政府明令维护佛教寺产。1931年5月,国民会议开会,太虚大师有《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就保护佛教寺产提出建议,经国民会议代表九世班禅向会议提出,并获得通过。8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维护寺产。 中国佛教会此时才获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认可。
此前主导中国佛教会的圆瑛法师虽然也当选常委,但在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时来函辞职 。圆瑛法师受到江浙丛林诸山、名流居士的拥戴,因为他的辞职,江浙诸山采取“不合作”态度,承认的会务经费无法落实,从而使迁往南京的中国佛教会会务陷入缓滞状态。落选的黄健六将致太虚大师的信函印刷分发,指责会议选举为不合法,更是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太虚大师因事态的混乱,于6月3日在《申报》声明辞职 ,领导中国佛教会前后不足两月。此后,虽有王一亭等人的协商挽留,但印顺法师则认为这意味这太虚大师主持中国佛教会的工作完全失败 ,同时,“与圆瑛间,乃不可复合” 。
太虚大师后来在《我的佛教运动失败史》中回忆,社会环境的激变,警醒了佛教僧众,于是有了中国佛教会的成立,本来是个非常好的开端,但因为外部压力的减弱,“旧僧制寺制渐安定而失却组织佛教会的原意” 。在《告全国佛教徒代表》中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庙产兴学已打销,再言整顿僧寺、兴办教务等,徒惹人厌!” 太虚大师对于中国佛教会的不满也反映出传统佛教僧团长期养成的惰性,一旦外部的压力减弱或消失,很快恢复到旧有的制度和观念。在给黄健六的信中,太虚大师还是在强调“欲建僧宝之住持,必为僧制之整理” 。
经历了两年左右的努力,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会颇感失望,终以声明退出的形式来结束了这样的“合作” 。太虚大师退出中国佛教会的声明一经公布,佛教界哗然,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佛教会纷纷致函挽留 ,诺那呼图克图也致函太虚大师,谓“若以悟道深邃之法师,亦宣布退出中国佛教会,则中国生灵之浩劫,将无穷期矣” 。虽然各方呼吁挽留,但太虚大师“于佛教会事,不预闻数年矣” ,不过,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会的瓜葛并未就此结束。1936年,他还试图参与改组中国佛教会 ,并作《对于中央民训部修订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之商榷》,对《草案》全部70条中的32条内容逐一提出意见。中国佛教会改组起因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民训部希望安抚反对中国佛教会的各省分会 ,达成团结,制订了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希望太虚大师可以参与改进中国佛教会 。对于这次改组,太虚大师本意想建立专属佛教僧尼的组织(应称“佛教僧寺会”)。在和民众训练部组织指导处张廷灏处长的谈话中,太虚大师强调“整理住持佛教本身之寺僧”,应由党政机关公布切实有效的寺产保持办法来安定全国佛教僧众的信心,同时,以训练僧中办理教务的人才入手,“渐进以整兴僧寺” ,这完全符合太虚大师一贯的佛教教团和整理僧伽的主张。然而,一场由政府发起、主导,太虚大师积极配合的改组,终因圆瑛法师、屈文六、闻兰亭、黄健六等人的阻挠而未获成功 ,太虚大师知道成功无望,发表《关于佛教会之谈话》 ,表面上无所谓的表示“但知余个人之乐得逍遥事外而已”。实质上,改组的受挫也体现了当时国民政府无视法令的真实面目 。何建明教授认为,“这次中国佛教会改组运动的中断,实际上宣告了近代以来的僧伽制度改革运动彻底流产,不仅对矢志推动僧伽制度改革以振兴中华佛教的太虚大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对中国佛教适应新时代变化的改进运动的一个沉重打击。”
借着抗战胜利的大势,1945年12月17日,终于在内政部与社会部的同意下,太虚大师领导成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 ,太虚大师、章嘉活佛、李子宽为常务委员。太虚大师发表了《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之诞生》 ,继续呼吁加强和健中国佛教会及各省市县分支会的机构 。后来(1946年7月),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在镇江焦山举办僧才训练班,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法师即为训练班的学员,曾聆听过太虚大师在结业典礼上的开示。遗憾的是,太虚大师于1947年3月在上海圆寂,仍然未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为了实现僧伽制度的理想,太虚大师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教团组织以作住持僧伽的号召,但终其一生,几经努力,收效甚微。在《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太虚大师悲观的宣告他所发动与领导的佛教革命运动完全失败。为何在当时复杂的教内外环境下,太虚大师仍然始终对中国佛教会抱持希望?印顺法师的说法或许正是一种答案:“对于中国佛教会,从旁赞助,正面主持,受排挤,受攻讦,明知不能寄予希望,而永久的萦回于大师的心中,怎样来整建教会,促成佛教的去腐生新,觉人觉世! ……大师心目中的佛教,是整个的,凡是有利于佛教,即使是维持苟安,大师还是愿意贡献他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太虚大师理想中的全国佛教统一组织得以成立。1953年5月,由虚云老和尚、喜饶嘉措大师、噶喇藏活佛、圆瑛法师等二十位知名佛教人士发起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 。在二十位发起人中,法尊法师、巨赞法师、赵朴初居士等人都是认同和支持太虚大师佛教改革者。特别是赵朴初居士在1980年代开始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带领全国佛教四众弟子开始了佛教复兴的大业。1983年,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