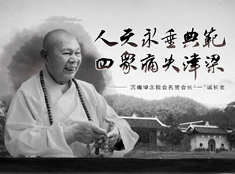“人生佛教”在当今国际佛教界已是一股颇具影响之思潮和引人瞩目的力量。此股思潮之启始开端者,乃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大师一生为“振兴佛教”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其目的则在建立“以人生为本位”、以“利益众生”为旨趣的“人生佛教”。值此大师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特从“人生佛教’’的角度,缅怀大师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近代“人生佛教”之缘起
中国佛教自“会昌法难”之后,从总体上说,已呈颓势。赵宋一代,除禅净尚存生机外,其余各宗,均趋式微。元、清二朝,由于皇族崇尚喇嘛教,藏传佛教有较大发展,然汉地佛教,仍不见起色。降至清季——如无言法师所说——“中国佛教史几乎是剩下空白的一页,是佛教最黑暗的时期”。(引自王惠霖《纪念一个宗教的革命大师》)当时之佛界,虽也有少数僧人、居士在为佛教之生存和发展而奋争,学术界也有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诸君热心佛学,然因时局动荡,战乱迭起,少数人之努力,终无能拯救佛教于颓危之中。
尤有甚者,当时之佛教界,许多僧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相反地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进而更衍为“超亡送死”之教,“避世逃禅”之地。这种现象,正如太虚大师对《佛教评论》的编者所说:“此我国僧尼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佛法不扬,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也”。
佛教遗弃社会的结果,是社会也遗弃了佛教。严酷的现实给当时的佛教界以深刻的反省,许多僧人、居士已开始意识到,不对传统的佛教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革新,佛教之存立已成问题,又遑论发展。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张,或曰:“在今日这种科学昌明的时代,佛教不改变方式是不能生存于今之中国的。”(《太虚大师纪念集》第一O三页)又曰“旧时佛教之僧伽制度,并渐变为农林工商以自食其力,势难存立。”(引自太虚《建设人间净土》)太虚大师更大声疾呼:“专就我中华佛教观之,固非有大加整顿,不足应时势之所趋,而适机缘之所宜也。”(《海潮音文库》第廿一卷,第七页)总之,佛教改革,势在必行,不改不足以适时应世,不改不足以求存立、图发展。问题在此,谁出来领导这场改革?怎样进行改革?
时代推出了太虚大师,大师也毅然以改革佛教为己任,他“研考规律,熟察环境,补偏救弊,统筹全局,而撰《整理僧伽制度论》”。(《太虚大师纪念集》第三十页)《整理僧伽制度论》的问世,是太虚大师致力于佛教改革的一个纲领性宣言。实际上,在此之前,大师早已萌发对佛教进行改革的念头。大约自光绪三十四年之后,受康有为之《大同书》、谭嗣同之《仁学》、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严复之《天演论》、章太炎之《五无论》及《民报》、《新民丛报》等之影响,他已有志于进行“佛教革新行动”。(太虚《告徒众书》、《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之后,大师一方面潜心研读佛典,旁及诸子百家,中西之学,为佛教改革作思想理论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创立各种佛教团体,创办各种佛教刊物,为佛教改革进行组织的舆论的准备。“而贯持此十年来救世运动之宗旨者,则由觉社丛书嬗生之《海潮音》月刊。”(太虚:《告徒众书》)
《海朝音》月刊之宗旨,据该刊之“出世宣言”称,乃“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太虚大师纪念集》第一O三页)所谓“大乘佛法真义”,按照太虚大师的说法:“小乘之究竟,惟在取得无余涅槃,所谓灭尽是;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海潮音月刊出世宣言》)此谓大乘佛法非是离世,而是人世的;不是只顾隐遁潜修,而是应该随顺世间,利乐有情。至于如何“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大师更有一系列明确诠释。如在《佛陀学纲》中,他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的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界,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太虚:《佛乘宗要论》)在《救僧运动》一文中,大师还明确指出:近代思想,以人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为本或以圣人之道为本。基于对近代思想,现世人心的考察,太虚大师看清并指出了佛教改革,必须走“人生佛教’’的道路:“末法时期佛教的主流,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进,即人成佛的人生佛教。”太虚:(《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二、“人生佛教”的特点
太虚大师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创立一种“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他不论著书立说、创办刊物,抑或组织各种佛教团体,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目的均在乎此。为了倡导、建设“人生佛教”,他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僧人、居士们也不乏主张佛教改革者在,但是若问“提倡人间佛教最热烈而诚挚者为谁”,无疑当首推太虚大师。
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所包盖广,既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内容,又有僧伽制度的组织整顿等。这里拟对其思想内容、特别就其思想内容的特色作一些探析。
“人生佛教”之思想特色,要而言之,大体有二: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人世”精神。
(一)以人为本
平常人认为,佛法是非人生的,太虚大师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大乘佛法就其“本义’’说,是“发达人生的”,“发达生命的完满生活的”,是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它不是离开人类而弄玄虚者,而是为化善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即使他读尽千经万论,也无异于“买椟还珠”。基于这种思想,大师认为,学佛当先从做人起。所谓学佛当先从做人起,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个人……做成有人格的人。”(太虚:《佛陀学纲》)只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说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人圣的佛陀呢?”(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此说平实亲切,但意蕴殊深。它把传统佛教中那种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及的“佛”直接植根于人生,改变了过去佛教与人生脱节,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认识到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先做成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便可“增进成佛”、“进化成佛”。这就是大师在《真现实论》中所说的“直依人生增进成佛”、“发达人生进化成佛”。
但是,在“人生佛教”中,佛教被判为五乘,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佛乘。就此五乘言,人乘与佛乘尚隔着天乘、声闻乘、独觉乘三个阶段,人乘何以能超越此三阶段而真达佛乘呢?太虚大师认为,天、声闻、独觉三乘“乃是人不走遍觉的路线得出的三种结果”,并不是从人至佛非得经达这三个阶段不可。就人与佛的关系来说,人好比一个小宇宙,而佛则是“全宇宙的真相”,是“人的本性的实现”、“最高人格的实现”,“人类得到最高的觉悟的就是佛”,“把人的本性实现出来”的就是佛。因此,人完全可以不经过天、声闻、独觉三个阶段而直接成佛,有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此即“即人成佛”之谓也。
(二)人世精神
太虚“人生佛教”的另一个思想特点就是主张亦出世亦人世。
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地方,即是小乘强调超坐离俗,注重出世求解脱;大乘佛教则提倡佛法不离开世间,世法即佛法,世法与佛法一而不二,世间与出世间融通无碍。正如法舫法师在《人间佛教史观》中所说的:“人世度生不离人间,……若离人间而谈大乘佛教者,直魔事耳,或仍不出外道二乘也。”太虚大师说得更直截了当:“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皆可读也。”(引自胡朴安《太虚大师不可及》)他还谆谆告诫门徒、学人:佛法并非隐遁清闲的享受,而教人不做事的。应对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故每人需要做正当的事业。例如,在自由社会里,应从事农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以这些作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可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在《复兴中国应实践菩萨行》一文中,他还号召学徒凡欲实行菩萨行者,应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则可服务于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使国家、社会和民众都能得到佛之利益。
注重利他,强调济世,这是大乘佛教相对于小乘佛教的又一殊胜之处,也是“人生佛教”所注重、提倡和大力弘扬的重要思想之一。在“人生佛教”看来,所谓菩萨,虽是出凡人圣之超人,但绝非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而应该同时是“社会的道德家”、“社会之改良家”。不论菩萨之人俗,抑或佛陀之应世,其所本者,乃“能舍已利他耳”。因此,“人生佛教”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释为“爱他”、“悯他”、“赞他”、“助他”,一言以蔽之——“利他”,并把此作为整个佛法的道德基础。
把“利他”精神贯彻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人生佛教”提倡“学佛应当去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等文章中,太虚大师反复告诫信众门徒:现在国家处在灾难之中,凡是国民都应该出来为救国救民尽一份责任。当有人问他:“你领导新佛教运动,为什么有些学生不住在庙里而从事其他工作呢?”他回答说:“我教育了他们,只要他们能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比住在庙里好得多。”(引自杨同芳《万方有难哭虚公》)抗战期间,大师号召佛门弟子积极投身抗战洪流,自己则率领佛教徒访问团至缅甸、印度、泰国等,联络同教感情,表示抗战的决心。
总之,既出世,又人世,强调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主张佛法既超脱世间又随顺世间,把“利他”、“济世”作为佛法之根本,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当然,这种佛教,不仅对于整个社会,即便就某一个人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对于“人生佛教”,实践问题有时甚至比理论问题更重要,建设“人生佛教”,显得比提出“人生佛教”意义更重大。这样,如何建设“人生佛教”——作为“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合乎逻辑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怎样建设“人生佛教”
建设“人生佛教”相对于“人生佛教”的思想学说,是个实践问题,但是,“怎样建设”自身又可进一步分为思想学说的建设和组织制度的建设两个方面。关于组织制度的建设,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等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这里拟着重从思想学说的建设方面,探讨太虚大师的有关主张。
从大师的有关著述看,思想方面的建设,还可分而为二:一是个人的,二是团体的或社会的。个人还可有“职业”、“志业”之分。佛教之职司者,则是僧尼。“人生佛教”之僧尼,应“先经出世之修证,乃进为应世之教化”;(太虚:《告徒众书》)至于“人生佛教”中之社会大众,则均得接受德、智、体、美四方面之教育。“德”即“志业”中之最高者——宗教(若佛教);“智”即“志业”中之次高者——理学(若玄学、哲学、道学、理学、科学等);“美”即“志业”中之其次者——艺术(若文学、音乐、书画、雕塑等);“体”即“志业”中之又其次者——游戏(若舞咏、游览、抛击、骑射等)。就个人说,虽然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职业”与“志业”可相摄相人,若政治家能同时为宗教之信徒或道学先生,那么,这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各种职业是相互联系、互相依赖的,“故能成为世界化之各业”,加之,各种“职业”、“志业”之间可以相互融摄,这样便能“成为一一职志的国际组织”,“果能各各成为一一职志的国际组织,不愁不能由其自然协调之关系,以成一总组合之全人类世界的和乐园。”(太虚:《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园》)
在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中,“人生佛教”常常更注重后者。例如,就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言,“人生佛教”虽注重个人人格之完善,但更强调集团之止恶行善和社会之利益安乐,这是因为当时之社会,非个人之恶止善行能达到救世拯民之目的,必须由集团之恶止善行乃能达成。又如对于“职业”与“志业”的相互关系,太虚大师喻之为“头脑与肢体”,头脑当然比肢体重要,故他说:“二业之中应志业为先也”。也就是说,在建设“人生佛教”问题上,大师最为注重者有二:一是“志业”的或曰精神的建设;二是集团的或曰社会的精神的建设。基于这个思想,大师指出:所谓建设人生佛教、人间佛教,“非弃置此恶劣世间,而另创造一个美善世间。当知世间美恶之分,皆由心之染净而别。”(太虚:《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园》)
三、“人生佛教”思想溯源
在考察论述“人生佛教”思想特点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人生佛教”在思想内容方面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有许多相近、相通之处。
儒家学说,虽源远流长,包罗广博,然究其旨归,可以一言以蔽之——“人”学。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思想史上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人”的发现;孔门“亚圣”孟子在历史上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第一次对人的本性进行系统的探索;宋明理学家们虽千言万语,主旨都是在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修心养性,成贤作圣。“人”的问题,始终是儒学最中心的问题,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足点,因此,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本主义的伦理哲学。
佛教自传人中国后,就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尤甚。例如,受儒家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整个中国佛教表现出一种由“佛本”而“人本”的发展倾向(这一问题笔者已另有专题研究,于此不赘)。这种倾向由禅宗而近代的“人生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对于《四书》、《五经》、老、庄、荀、墨甚乃康、梁、严、章之书无所不读,深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底蕴,对儒家的伦理学说尤其精通并深表赞赏,认为中国二千年来文化主流在儒,“屡言中国文化之特点,在于本人情为调剂之人伦道德。”(太虚:《附书与仇张二君谈话后》)且一再指出,儒家这种伦理学说与佛教的思想毫无“间隙抵排之端”,而是可以遥相契合,甚至“水乳交融”,因此,主张“孔学与佛学,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毁”。(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
在太虚的许多著作中,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孔子是人乘之至圣,儒学可以作为“人生佛学”之基础,并且认为,儒学是中国二千年文化之主潮所在,故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时,这种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人生佛教”“亦最适宜为各国倡”,谆谆告诫西行学人,应该把中国文化之人伦道德“披四海”、“垂下世”,可见大师对于儒家人伦道德之学的赞赏和推崇。
太虚倡导的“人生佛教”,还十分重视把“国民性的道德精神”贯彻于实业、教育、军警、政法之间,并把它作为“纲格”、“维制”,认为这是中国人实行自救的唯一办法。而所谓“国民性的道德精神”又是什么呢?太虚认为就是“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而此“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大师指出则是冶三教于一炉的“宋明化之国民性德”——即“理学”。“理学”又称“新儒学”,尽管“新”,毕竟仍是儒家之学,当然,准确点说,是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的儒家学说,可见,儒家思想,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人本主义伦理哲学,实是“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人生佛教”的另一个思想特点——人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儒家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
儒家自孔子开始就主张“重人事、远鬼神”、重现实、轻玄想;至《孟子》、《大学》、《中庸》乃至宋明理学,更大讲“修、齐、治、平”。主张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以“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标。宋明之后的许多儒者,更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这种“人世济民”、“经世致用”思想,对整个中国佛教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致历史上凡是中国化色彩较浓的佛教宗派,都反对传统佛教的超尘离俗、隐遁潜修的作风,而主张世法即佛法,人世即出世。太虚倡导的“人生佛教”,也具有这一特点。太虚本人就一再指出“遁迹山崖”、“离世隐修”是导致佛法不扬、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比潜形山谷、隐修寺庙更好。这种思想与儒家“人世”、“用世”精神是遥相契合的,或者说是受儒家人世精神长期影响的结果。
当然,指出“人生佛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儒家“人本”和“人世”色彩,丝毫不排除“人生佛教”是“原本于释迦佛遗教”。实际上,佛教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大乘佛教已在讲“慈悲普度”、“利生济世”,中国历史上的禅宗更注重人生,强调人世,提倡“即世间求解脱”。因此,从佛教自身的思想渊源说,“人生佛教”实远承大乘佛法,近接中国禅宗,是大乘佛法与中国近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