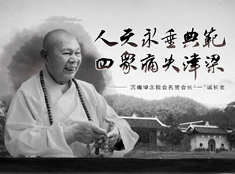辛亥革命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维新思潮风起云涌,佛教界也随时势的变异掀起一场改革复兴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虚大师的整顿僧伽制度运动。
清末民初,在社会骤然剧变的大格局下,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佛教也进行了自身的改造、调整,吸收了中西古今的各种学说,力图迎合时代的演变,因而出现了民国以来的改革中兴气象。太虚大师在这一新思潮的影响下,也希望在佛教界进行改革,有所作为,遂于1912年到南京组织了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想把镇江金山寺改为佛学堂。但由于佛教界传统势力的阻挠,协进会与佛学堂不日而夭。1913年2 月,太虚大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号召重视人生,回报社会,复兴佛教。1914 年,太虚大师到普陀山闭关3年,将其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整理,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出关后,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高举佛教改革的旗帜,提出“三种革命”,开始了他为时30年的改革实践和弘法事业。
太虚大师所谓教理革命,其重心在革除已往佛教专为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政策的工具,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再配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以此改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增进人类互助、互敬,完善社会制度,使人人能注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展,谋求进步,以道德来美化人生、发挥人生本有性能,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并极力排斥类似神道设教及专向死后问题的探讨。
所谓教制革命,太虚大师在所著《僧伽制度论》中作了专门的论述。这也是三大革命的重点所在,目的在于改革僧伽制度。后来他又写了《僧制今论》、《建僧大纲》等进一步阐述他的改革主张。太虚大师反对深受我国传统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反对把住持当作家长,将徒众当作子弟,呼吁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使其适应时势,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形成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以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戒和同修、意和同悦的精神,使僧团成为弘扬佛法的中心。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全国10万僧伽为准,构想了一个理想僧制的组织蓝图。以他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团”,它是总部机关,包罗宏富,总摄僧俗;各省再设立一“持教院”,是为一省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派建各宗寺,作为八宗的专修场所;每县则设1个“行政院”(县佛教团体机关),1个“德苑”(专修经忏法事),1个“尼寺”(专住比丘尼),1个“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4个“宣教苑”(宣讲于乡镇)。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这是一套完整并富有启发性的理想僧伽制度,但由于这种想法距离当时现实僧团实际太远了,最终难以付诸实施。
所谓教产革命,就是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不为少数住持所私有,要用之以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才和兴办各种僧伽教育事业以及社会慈善事业,如办学校、医院、工厂。在这三大革命中,教制革命为其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革命和教产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审时度势,倡导整顿僧伽制度,力图补偏救弊,主张统筹全局。他的这一主张,吸引了当时教内外的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其所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三项重点内容。正如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所说:“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下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具体来说,一是革除历代帝王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二是改革避世隐遁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改革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三是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我国僧寺制;建设我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建设奉行十善规则的民俗及社会。
这三项主张,是太虚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但总的来说,太虚大师的革新计划没有获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佛教内部强大势力的阻挠,传统力量过于强大,并认为这些改革的主张是离经叛道。太虚大师晚年写有《我的革命失败史》对其改革运动作了总结。这一佛教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实在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与总结。尽管说太虚大师改革僧制的理论是继“百丈清规”以后在佛教制度建设方面的又一创举,其培育僧才,兴办文化事业,功绩多多,但其倾心力最多、最大的僧制建设却是失败的。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未能契合当时僧团之机,且整顿之时节因缘并未成熟,思路尽管是超前的,但结局却是令人抱憾的。